
这场资格赛已经进行了四个多小时。发牌的荷官面容疲惫,时不时打个哈欠,手上却依旧利索,发牌、揽筹码、切牌、翻牌。
中央发牌区的绿色绒布外圈用白线划分出了九个位置。比赛进行到此时,牌桌上只剩下最后四名选手。一号位的老赵、三号位的馒头片、四号位的Tonny,以及六号位的我。
就在刚刚结束的一把牌里面,原本筹码量第三的老赵,把全部筹码输给了馒头片。他瘫坐在黑色的皮质大转椅上,因为紧张和闷热,干燥的脸颊泛着红,紧锁的眉头透出不甘心。荷官没有着急赶老赵离桌,让他坐在那里抽完最后一支烟。
“哎,老赵太冲动了。”
“我觉得可以推的,只不过碰上了,没办法。”
“馒头片今天运气太好了。”
“还是不应该推,筹码还那么多,不值当,打比赛要有耐心。”
被淘汰的选手需要离开比赛房间,T先生、CC和另外几个人站在门口,观看着牌桌上的局势,时不时讨论两句。
凌晨两点,荷官洗好牌,比赛还在继续。
十一月底的北京已经很冷了,豪胆之星里面却是燥热的,弥漫着紧张的气息。这是2011年全国扑克嘉年华CPC的资格赛,前两名可以获得CPC的参赛资格和酒店住宿,价值5500元。
剩下的三名选手中,只要再淘汰一人比赛就结束了。
被淘汰的那个人无疑是今晚最倒霉的家伙,奋战四个多小时,最终一无所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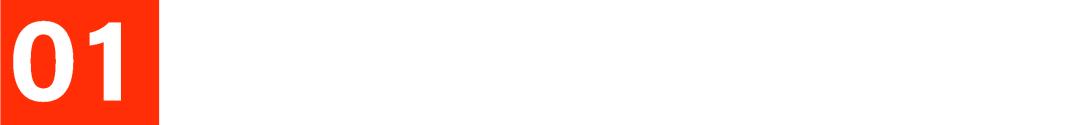
开始玩德州扑克是2011年初,当时我刚开始和T先生约会。一天下班,他说有几个朋友在茶馆打德州扑克,要不要一起去。我说,不会,没玩过。T先生用了一个小时跟我讲规则,还给我了一张卡片,上面写着成牌的大小。同花顺大于四条,大于葫芦,大于同花,大于顺子,大于三条,大于两对,大于一对,大于高牌。对于从小不玩扑克的我来说,这些东西看起来就像是密码。
我拿着卡片,跟着T先生走进逐鹿茶楼的一间茶室。六七个人已经围坐在长桌上开始玩了。这个朋友局核心的几个人是清华校友,二十七八岁的年纪,大多都有留学背景,在海外的时候开始玩牌。坐在最里面的年轻人叫张超,是他邀请的T先生。那时,德州扑克还没有在国内火起来,玩的人不多,虽然我和T先生都不是清华的,但还是被欣然接纳了。
“一个人玩,还是两个人玩?”张超问。
“两个人玩。”T先生说。
我给T先生使眼色,“要不我先看看吧。”
他说,“输了算我的。”
张超转过身,从身后的筹码箱里拿出来两摞筹码,一摞递给T先生,一摞递给我。这是我“德扑生涯”的开始。
第一次玩德州扑克,搞不清牌面大小的我,竟然成了当晚最大的赢家。这可能就是所谓的“新手运气”。后来我知道,留在这个游戏里面的,通常都是一开始赢钱的,不管赢多少。
T先生夸我有天赋,正式收我为徒弟。于是德州扑克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,成为约会的主要内容。最夸张的时候,我们不是在打牌,就是在研读教学书籍,或者看德扑视频。
“为什么这些人要戴墨镜?你看这个人,又是帽子又是墨镜。”我们窝在不大的出租房里,看前一年的WSOP比赛,我随口问T先生。(WSOP即世界扑克锦标赛,每年夏天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,2021年的WSOP的主赛有6650人参加,总奖池超过6200万美金。)
“为了装酷吧。真正的高手不需要这些,你看Tom Dwan、Phil Ivey,他们都不戴墨镜。”T先生相信Poker Face是思考状态的自然呈现。诈唬需要的并不是勇气,而是知道对方手牌的范围,你只能吓走那些本来牌就不够强的人。
那要怎么才能知道对方手牌范围呢?经验是一方面,概率是另一方面。
所以T先生给我的教学都是从计算赔率开始的。他甚至会拿出纸笔,给我证明,为什么从数学上来说,翻牌前敞开加注(open raise)三倍大盲是最优策略。
在学习德扑的过程中,我渐渐体会到博弈论的奇妙与平衡,也享受于思考的乐趣。

德州扑克有两种游戏方式,像我们在茶楼一帮朋友一起玩的,是现金局。和打麻将一样,在麻将里面大家会约定“一番”多少钱,在德扑现金局里面,大家约定好一个“大盲”多少钱,之后就一直按照这个玩,中途谁不想玩了可以随时离场。
还有一种方式是锦标赛。与现金局不同,锦标赛是封闭的,选手买票入场,每个选手获得数量相同的筹码,当手上筹码全部输光,即淘汰出局。随着比赛的进行,盲注会相应的上升,使比赛节奏加快。最后,所有人的筹码会聚积在一个人手里,这就是冠军。这是一个赢者通吃的游戏,只有排名前10%-15%的选手可以瓜分奖池,第一名通常可以拿走其中的一半。
2011年,想在北京打锦标赛并不容易,豪胆之星扑克俱乐部可以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。这是全国第一家以德州扑克为主题的俱乐部,位于北京日坛公园北侧的步行街上。
第一次去豪胆之星是在夏天。远远看见一片漆黑中亮着大大的霓虹招牌“Hold’em Star Poker Club”,下面是一行中文小字“豪胆之星扑克俱乐部”。Hold'em是德州扑克Texas Hold’em的简称,“豪胆”应该是hold'em的音译,真是个好名字,有豪情、有胆识,牌友们都这么自居的。
推开大门,最先扑过来的是久散不去的烟味,我不禁咳嗽了两声。然后是明快的爵士音乐和隐约传来的嘈杂人声。一楼布置得像一个酒吧,一进门是休闲区,有台球桌和飞镖。上二楼的楼梯下面藏着吧台,吧台右侧是六组卡座。两面墙上挂着电视,循环播放着“High Stakes Poker”(高筹码扑克,是2011-2012年期间非常火的一个德扑真人秀节目)。
然而一楼并没有人,吧台后面也没有调酒师。所有人进门后,径直从左侧的楼梯上二楼。嘈杂的人声就是从那里传进来的。
二楼楼梯口有一张小桌子,一个工作人员坐在后面,参加锦标赛的选手需要在这里买票。那天只有常规的日赛,我和T先生各交了200元报名费,拿了一万筹码和座位号,走向牌桌。
第一次在专业牌桌打牌,参加有荷官的比赛,我紧张得心脏噗噗直跳,学着别人的样子假装镇定。虽然打德扑也有小半年了,但是锦标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牌桌上面对的都是陌生人,有戴着金链子不停摆弄手机的年轻人,有抽着烟戴着大钻戒的姑娘,有一脸严肃紧皱眉头的大哥,还有不停和你说话的中年大叔……
我当时二十出头,工作了几年算是见过世面,穿着打扮也已经不是学生模样,但内心却很惶恐。好像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只有我不知道。
由于紧张,在第一次下注的时候,手一滑,筹码掉了一半,我赶紧把散落在后面的筹码推进筹码池。荷官警告我,要一次性下注。我想我当时脸色应该难看极了。整场比赛,我都在担心因为犯错而不敢行动,像只鸵鸟,埋着头等好牌。很快我的筹码就所剩不多了。
一般小型比赛为了填充奖池,比赛前期选手可以无限次买入,也就是说,选手在输光筹码之后,可以再次买票参加。当比赛进入停止买入阶段,每个选手就只有一条命,筹码输光就彻底出局。
我的第一场锦标赛无疑是失败的。我是全场第二个被淘汰的,但是坐在比赛桌上的那种紧张和兴奋感,好像只有小时候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有过,非常让人振奋。当然,被淘汰之后的懊悔和不甘心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迫切地想要自己变得更强。
后来我和T先生成为豪胆之星的常客,几乎每周都会去一两次。

十一月底的一个周五,我和T先生一下班就急匆匆地出发了,从西北四环到东南三环,跨越整个北京城,抵达豪胆之星。逃离寒冷的街道,钻进俱乐部,顿时感到温暖,加上比赛的火热氛围,甚至有热烘烘的感觉。
资格赛已经在豪胆之星打了有一阵了,这是2011年冬天最热门的比赛。据说在12月,会有超过500位德州扑克选手汇聚三亚,在此之前,国内没有举办过任何超过100人的德扑锦标赛。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中国扑克嘉年华(CPC)资格赛。
拿了筹码,我和T先生一起坐上牌桌。
“来了?”馒头片坐在我斜对面,自然地跟我打招呼,同时低下头翻看自己的手牌,“一晚上都这小破牌,你不能给我发点10以上的牌啊?”说着把手牌扔进牌堆,斜着眼睛对荷官说。
馒头片看上去三十出头,穿一件带毛领子的大衣,脱下来搭在座椅背上。她不太化妆,皮肤很白,但被熬夜带来的疲惫涂了层灰色。
“对啊,还没打到票呢。”我坐下,整理好筹码。
“我昨天晚上第三,被CC bad beat了,AA输给对十。”馒头片是北京人,说话很快,皱着眉头,颇有大姐大的派头。说完,拿出一软烟盒,敲了敲,夹出一根烟。
Bad Beat,缩写BB,翻译过来是“小概率击败”,是每个玩德扑选手的噩梦。以馒头片说的为例,她拿一对A,CC拿一对十,如果两人在翻篇前把全部筹码押下去,那么一对A有大约80%的胜率。而结果却是CC的一对十赢了,20%的小概率发生了,馒头片就被BB了。
每个德扑牌手都有被“小概率击败”的惨痛时刻,那种不甘心和气愤,就像是被人无缘无故地在脸上打了一拳。然而,一场锦标赛,要从几十人、上百人里面胜出,你需要运气站在你这边,也需要在关键时刻BB别人。通常人们总会记得运气离你而去的时刻,却忽略了她站在你这边的时候。
“呀,馒头片昨天晚上bubble了啊?”Tonny坐在馒头片右手边,幸灾乐祸地说。Tonny大概二十六七岁,游戏人间的富二代海龟,寸头修理得很有型,白毛衣,有一张很好看的脸。站起来应该有一米八,但那次他左腿从脚踝到膝盖打着厚厚的石膏,说是去长白山滑雪摔的。
“太tm倒霉了!”馒头片说着,低头看了一眼手牌,拿起一摞筹码,“加注!”
“哎呀,生气了啊?要不起,赶紧跑。”Tonny笑嘻嘻地把手牌扔进牌堆。
Bubble,气泡,是说在锦标赛里面被排除在钱圈外的那个人。例如在这场资格赛里面,前两名能拿到CPC门票,第三名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仅剩三个人的时候,就是气泡时刻。通常这个时候大家都会非常谨慎,谁都不想“被气泡”了。而真正的高手会在这个时候利用对手的恐惧心理,大肆加注、抢盲注,来累积自己的筹码。
这时候,CC靠在门口向屋里张望,被Tonny看到,“说曹操,曹操到!刚还说你昨天BB了馒头片呢!你现在手上几张CPC票了啊?卖给我一张吧?”
“有三张,你先自己打,打不到再来找我买。”CC叮嘱自己的小兄弟,笑着转进了隔壁的一间屋里。
“那人就是CC啊?听说特厉害?”牌桌上八号位一个胖胖的男生问。他应该是新来的,面生。
“还行吧,他老早就在澳门打比赛,接触得早。”桌上另一个人说。
德扑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一起打过牌的人,很少有人承认别人打得比自己好。别人赢牌都是靠运气,自己赢牌都是靠实力。
2011年的时候CC也就三十出头,但算得上中国德扑圈元老。他个儿不高,娃娃脸,眼睛大大的,打牌非常专注和认真。听说他曾经想做职业电竞选手,没有成功,后来在游戏杂志做记者。一次出国采访,CC接触到德扑锦标赛,觉得很有意思,就开始打牌。
大部分人打牌就是图个乐子,随着心情打,跟大爷大妈退休打麻将一样,但有企图心的牌手会学习、思考、总结。他们不打很多手牌,但每次都力求决策正确。CC和T先生都属于这个风格的。

比赛进入到了停止买入的阶段,气氛一下变得严肃起来。这把馒头片在翻牌前加注,两家跟。公牌出来,馒头片下注,八号位那位胖胖的男生加注,另一家弃牌。连续三轮下注,八号位选手都非常凶猛的选择了加注,最后一轮,馒头片顶不住了,弃了手牌。
八号位选手开心地揽下了筹码池,亮出自己的手牌。两张小牌不同色,和桌面上的公牌一点关系没有。随即,牌桌上传出“wow”的起哄声音。
有句话说,永远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底牌。这种诈唬之后又亮出底牌的做法,既不礼貌,也不聪明。有的人会把这个当作是秀肌肉,你看,我什么手牌都能玩,我什么都没有照样赢你。但对于高手来说,任何信息都可以被利用,亮一次手牌就透露了一个模式。下一次如果你用同样的加注模式,那么你手牌的范围就会被预估到。
真正的高手是变换莫测、不可预估的,而这样的高手我只在电视上见过,大部分人都有自己明显的打牌惯性而不自知。
诈唬后亮手牌还有一个作用,就是让对手恼羞成怒。有些人被诈唬后,自尊心会受到极大的伤害,气愤,懊悔,自我怀疑,进入情绪的旋涡,不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。这个状态叫做Tilt。如果一个牌桌上有人Tilt了,那么ta将成为整桌的攻击目标。
然而馒头片可不是吃软饭的,八号位亮出手牌的那一瞬间她是愤怒了,当即爆了粗口。但这点儿波折不会影响她后续发挥。她点了根烟,对着8号位露出轻蔑的微笑。
果不其然,八号位很快就因为再次诈唬被抓,筹码被T先生咬掉一大半,剩下的没多久也都输光,离开了牌桌。人一走,馒头片就放声大笑,报了仇似的快乐。
随着比赛推进,不断有人被淘汰,剩下的选手会合桌,四桌合成三桌,再合成两桌,最后都合在一桌。这一桌叫做final table,决赛桌。合并决赛桌之前,我筹码已经不多了,也就十个左右大盲,是桌上的短筹码。根据《Harrington关于无限比赛的专家策略》一书,这个时候只要位置好,不论什么牌都应该全押。
进入前九名,坐上决赛桌,并没有什么意义。在这场资格赛中,只有前两名才有奖励。但决赛桌是个荣誉,大家都不想在合桌的时候被淘汰,这让选手们变得不合逻辑地异常谨慎。
保持理性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,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投行大佬、股票交易员、创业者推崇德州扑克。它就像是一个决策沙盘:一个基于错失的恐惧,一丝基于屈辱的愤怒,一个基于贪心的侥幸念头,都会毁了整个计划。
越是在恐惧的氛围里,越要勇敢。“All in!” 我坐在庄家位的右侧,我身后的庄家位、小盲位、大盲位都选择了弃牌。就是这个时候,我推进了全部筹码。
在德扑牌桌上,大家往往对于女生会有“诚实”的固有印象:当一个女生推出她的全部筹码,那么她一定有很大的牌。说是诚实,不如说是对女生软弱的刻板印象。诈唬是需要胆识的,而胆识,是女生没有的。
我先后在德扑桌上遇见过许多女生,我们心照不宣,牌桌上对女生的这个刻板印象几乎成为我们最大的优势。每当我们用小牌吓唬走其他选手的时候,他们认定我们拿到了nuts(最大的成牌)。当然,不要亮出底牌。
同样在决赛桌之前打得比较凶猛的是T先生,但今天运气并不站在他一边,两次接近50%赢面的全押对决都输了,在决赛桌之前淘汰出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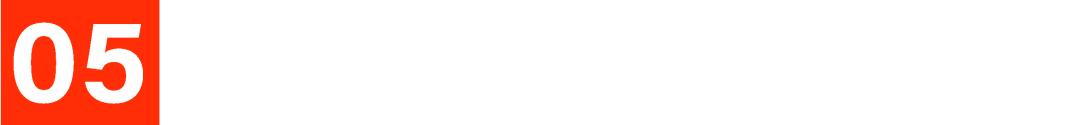
合桌的空隙比赛暂停,选手们纷纷离开牌桌,在休息区域休息。
德扑锦标赛真是体力活,这样一场三四十人的资格赛都需要四五个小时,大型比赛,例如WSOP的主赛通常需要好几天才能结束,对选手体力和注意力都有很高的要求。
休息区域,选手们做着各种拉伸动作,同时拉着同伴复盘之前的牌局。T先生也拉着我跟我说之前犯了哪些错误,接下来应该用什么策略。我努力听着,但感觉脑袋已经不太转了。
“我好累啊,反正我是短筹码,推就好了,看命了。”我无奈地说。
“短筹码有短筹码的优势,看准时机。”T先生最后交代道。
所谓短筹码就是说筹码少的意思。在锦标赛里面选手们的起点是一样的,但是随着比赛进行,每个人手中的筹码数量会变化。全场筹码最多的人称作Chip Leader(CL),全场总筹码除以剩下选手数得到的是平均筹码,多于平均筹码通常被认为比较安全,而低于平均筹码就称作“短筹码”。
筹码多少决定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应该采取什么策略。例如CL应该用自己的筹码量去给其他选手施压,因为同样一把牌,双方全押,如果筹码少的选手输了将离开比赛,而CL输了只是输掉一些筹码。同样的,对于短筹码选手来说,因为筹码太少,靠等待是等不到最后胜利的,需要找机会让自己翻倍,光脚的不怕穿鞋的,不如找机会和人比拼,结果就看运气了。
选手们回到牌桌。此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,比赛剩下9个人。CC目前筹码量第一,大幅度领先于其他选手,馒头片排第二,Tonny在平均筹码水平,而我和老赵则属于短筹码,不到15个大盲。
预测比赛结果还为时尚早。
此时牌桌出现一把牌,公牌已经发出来四张,有三张红桃,同花牌面。在局内的有两家,CC和Tonny。转第四张公牌的时候CC过牌,Tonny全押,CC秒跟。CC手中的牌明显已经成了同花。
荷官数好双方筹码,示意两家亮牌。CC甩出AJ红桃,果不其然,和公牌的三张红桃组成了同花。Tonny的眼神露出一丝绝望,“我就知道他成花了!”他在椅子上喘着粗气。
在牌桌另一头的CC直勾勾地盯着Tonny,面无表情。
大概过了五秒钟,Tonny大叫一声,亮出自己的手牌,是一对儿6,和公牌里的红桃6,组成了三条。房间里有叫喊声,也有叹息声。
“Tonny,这个牌怎么能打这么大呢?你还那么多筹码,没必要跟CC对上啊!”老赵扼腕叹息。
此时,所有人都站了起来,包括打着石膏的Tonny,他把整个身体的重量放在胳膊上,撑着牌桌,双眼紧紧盯着河牌的位置。Tonny唯一赢CC的可能就是在河牌(最后一张公牌)的时候中四条或者葫芦(三条加两对),而这概率小于20%。
荷官拿起牌堆,切掉一张,下一张扣着放在河牌位置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,不管谁赢,比赛格局都会被打破。
荷官熟练地翻开河牌,是一张6。
房间里充满了尖叫声,Tonny兴奋地跳了起来,摔下来的时候发出惨叫,但他顾不了那么多,激动着尖叫着,用拳头砸着牌桌。
要知道“四条”是非常小概率事件,今晚幸运女神在Tonny这里逗留。CC嘴角的微笑僵住大概十秒钟,然后摊摊手,坐在了座位上。
荷官把一大堆的筹码从牌桌中央推到Tonny面前,Tonny翘着脚艰难地坐下,不慌不忙地整理筹码。
比赛继续,荷官开始发牌。大家已经从刚才的兴奋中恢复过来。
“Tonny啊,今天是你运气好,但这个牌真不应该这么打。时间长了会输大钱的。”老赵语重心长地说。
老赵应该有四十了,微胖,发际线已经向后走了不少,说话不紧不慢。我一度以为他是豪胆之星的老板,因为不管什么时候来,他都在,而且和每个人都很熟。打牌的朋友也就是在牌桌上聊几句,我们从来不问对方的职业,成家了没有,但老赵似乎对每个人的情况很了解,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一年多以后,他去了新开的俱乐部做赛事监督,我才知道2011年时他和我们一样,只是爱好者。
对于这些来打牌的年轻人,老赵很是关爱,深怕他们走错路。Tonny听到老赵的“教导”,赶紧点头称是,毕竟赢了嘛,心里高兴,被说两句不打紧的。
另一头的CC也有话要说,“Tonny你需要反省一下,今天要不是你狗屎运,你就折我这里了。决策的好坏是不以结果来衡量的。要记住,不要以为赢了,就没事了,错了就是错了。”
赢输不重要,重要的是打对的牌。这是德扑圈的名言。一手牌有很大的运气成分,再小概率的事件也有可能发生。但是只要你坚持做对的决策,打一万手牌,十万手牌,长期来看一定是赚钱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初中数学里面学的“期望”,期望是正的,只要重复足够多次,结果就是正的。
好的德扑选手懂得自律的重要性,严格按照期望价值做决策,不会有侥幸心理,输了也不会有不甘心。这都是需要刻意练习的。

随着盲注的增加,比赛节奏进一步加快,筹码在每次对决中流动,不断有人淘汰离场。CC在Tonny那边输掉了一大半筹码,后来又和我对了一把牌,运气依旧没有站在他那边。剩下一点筹码三两下就输光了,淘汰离场。
此时牌桌还有四个选手,Tonny是CL,馒头片和老赵筹码量相当,分别排第二金额第三,我一直是短筹码,苟延残喘到现在。
老赵和馒头片对上的这把牌,大家打得都很谨慎,因为双方筹码量差不多,伤着谁都是致命的。公牌发出来之后,馒头片应该是中了一对,她下注,很明显是要劝退老赵。
老赵平时随和,打起牌来却非常严肃。他面无表情,呼吸沉稳而均匀,不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馒头片。
“想啥呢?我肯定成牌了,快弃了吧!”馒头片不耐烦地叫唤起来。
漫长的寂静,所有人在等着老赵做决定。
“荷官,计时!”馒头片要求荷官限制时间。这个是常规操作,如果一个牌手占用太多时间思考,其他牌手可以要求倒计时60秒,催促他做决定。
老赵依旧面无表情,不慌不忙,看着60秒一秒一秒的过去。“全押!”他说,然而表情看上去相当绝望。
“为什么啊?”馒头片大叫起来,“我俩这筹码都这么多,好好待着不好嘛!”他们此时的最佳策略应该是联合起来,先把身为小筹码的我“干掉”,而不是互相伤害。
“行吧,你要比就比吧!”馒头片跟了。
结果老赵并没有等来他要的同花叫牌,馒头片的一对赢了,老赵的所有筹码拱手送给了馒头片。
于是我们到了开篇的那个场景。比赛剩下三个人,馒头片成为新的CL,Tonny第二,我第三,筹码少得可怜。比赛进入泡沫阶段,对于两个大筹码加上一个短筹码,此时策略非常简单,就是他们两个轮番加注,来抢我的大、小盲,直到我筹码耗尽出局。
而我打算用破罐子破摔的策略,坚决抵抗,不能让他们的偷盲策略成功。所以他们的每一次加注,我都用全押来反抗。不得不说,那晚我运气不错,赢了Tonny一次全押,让我筹码翻了一倍,又赢了一些他们的加注筹码,很快筹码量就超过Tonny了。
现在位置翻转,轮到我和馒头片上演巧取豪夺的戏码了。Tonny似乎没有适应迅速到来的权力位置变化,一下乱了阵脚。他焦躁地反复看着自己的手牌,好像再看一次牌就能变得不一样。他在等待一手可以让自己翻身的好牌。但从他骂骂咧咧弃牌的样子就可以知道,他的手牌一把比一把差。
Tonny的筹码在他绝望和焦躁的情绪中迅速消耗。
最后一把牌,Tonny剩下五个大盲,馒头片在庄家位加注,我在小盲位弃牌。Tonny没有其他选择,没看手牌,坚决地推出所有筹码。他早该这么做了,在三个人的局里,手牌并没有那么重要,位置和局势判断才是关键。
馒头片跟注。
荷官示意双方亮出手牌。馒头片是A3,Tonny深吸一口气,拿起手牌使劲甩出去,是K10。
“不错!有戏!”对于Tonny来说,在不得不全押的情况下拿到K10这样的牌算是很幸运了。公牌发5、3、J。我和馒头片不约而同地跳了起来,喊出“Yes!”馒头片中了一对3,领先。
Tonny撑着一条腿也站了起来,冲荷官说,“接着发,接着发,还有希望。”
转牌一张8,河牌一张2。馒头片赢了,我赢了,比赛结束。
Tonny慢慢坐下,戏剧化地摊开双手,边摇头边对馒头片说,“没办法,没办法啊!”馒头片一脸得意,冲着Tonny说,“对不住哈,今天你Bubble了,哈哈哈!”
房间里传出欢呼声,T先生冲进屋,给我了一个拥抱,说,“太好啦!赢了!”
兴奋夹杂着疲惫,我靠在T先生身上,长叹口气,“啊!太不容易了!一路小短码坚持到最后……”
“坚持就是胜利!”T先生笑着说。
馒头片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,拍拍我的肩膀,“配合不错!”
临走前,工作人员给我们合影。馒头片穿上毛茸茸的大衣,拿着红色的海南CPC比赛门票信封,搂着我的胳膊,我们一起冲着镜头傻乐。
“今天赢的是两个女将啊?”摄影师喃喃自语,按下了快门。
走出俱乐部,深夜的寒风冷冷地吹过来。凌晨两点多,漆黑的街道上,豪胆之星的霓虹灯在身后闪烁。
一年后,德州扑克将会在中国流行起来。我和T先生隔年开始创业,工作越来越忙,俱乐部去得越来越少。后来,离开北京,周围没有什么打牌的朋友,德扑也就很少打了。
老赵一直在为数不多、依旧存活的俱乐部组织和承办德扑锦标赛。
Tonny腿好了之后,没有出现在后来的那些新俱乐部里面,可能出国了,可能结婚了。
馒头片又打了一年牌,成为了一个职业旅行家,每年200天在世界各地看野生动物,上天下海,偶尔路过一家赌场,进去玩两把德扑,还能赢点钱。
CC做了两年职业牌手,在很多大型德扑锦标赛里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,后来加入了一家游戏公司做德扑App,再后来就不得而知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